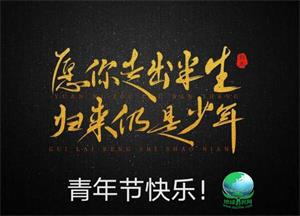我的父亲韩志俭生于1921年4月26日(农历)。他兄弟姐妹九人,他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一个弟弟,他排行老八。
父亲这个大家庭在当地是很有影响的。从爷爷那一代开始,就把这个家族逐步打造成一个耕读之家。凡是男子,不管家庭多么困难,农活儿有多繁忙,也要在农闲时节进冬学读几个月书。为此家族专门请了先生给父亲的兄弟们教书识字,附近的孩子也可以进我们家办的冬学上学,所以父亲这一辈的男子都有一定的文化。
我们家大约是临近解放的1947年从东胜的巴音敖包搬迁到杭锦旗的原白音补拉苏木锡尼补拉大队的,原来叫旧营盘壕,民间则称“黑地”。因为解放前父辈们就在这些地方租种牧民土地(当时叫经 “牛犋”),所以感到牧区不仅土地肥沃,肥料也很好解决,牛粪、羊粪遍地都是,而且土地资源也特别充沛。
迁到牧区后,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和二伯父、三伯父住在一个顺土坡开挖的一溜窑洞里。后来条件好了,我们家才搬到东面的开阔地盖起了房子。后来,大约是62年前后吧,三伯父他们也都搬了出来。和我们家住得也就2里地远。因为三伯父家有6个孩子,还送给别人家一个女孩,生活十分拮据。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挺过来的。二伯父在大营的供销社工作,距离我们也不远,也就是10几里地吧。他的儿子、我的三哥一直和我们家做邻居,在一起住了大概有20多年。二伯父有时候春节回来和我们过年,难得团聚一次。五叔父在另一个公社,一生务农,离我们家也不远,也就15里路吧。大伯父住在东胜县的巴音敖包公社,也就是我们的老家韩家渠,一辈子务农。在我的印象里,他的身体不是太好,老是咳嗽,但还不停地抽烟,所以弟兄五个就他去世得早。
爷爷去世得早,我没有见过,奶奶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也不时被三伯父和五叔父接去家里尽孝,但只要住上十天半月,父亲便派我骑上马或驴,赶快去把奶奶接回来。父亲的二姐、我的二姑去世得最早,后来大姑也去世了,怕奶奶接受不了,一直瞒着她老人家,只有大姑夫有时回来看望奶奶,后来大姑夫去世后,大姑这个家族基本就和我们家断了来往。三姑居住在巴彦淖尔市的磴口县附近的一个农场,那时交通不方便,所以回来一次十分不容易,在我的记忆里,就不曾有过三姑住娘家的印象,我也不曾见过那三位姑姑。只有四姑住在东胜县巴音敖包的孟家渠,离我们家也就是30多里地的样子,每年四姑都会来住娘家。所以每年的农闲时分,父亲便会派我去接四姑来住娘家,这也是唯一和父亲来往最多的一个姑姑。
年幼时,家庭兄弟姐妹多,所以父亲从小放羊、拾粪、掏柴、帮牛,凡是孩子们能干的活儿,都有他的份儿。后来倡导“耕读之家”的爷爷让他冬闲时读了几年“冬学”,见他很有天分,后来又送他到附近的私塾读了几年小学,加上自己的努力,在当时的农村来说,他也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
在国民党时期,他相继担任过甲长、保长,在当时的东胜县智勇乡当过管理财政的副乡长,加入过国民党,也当过兵,还曾经在东胜县附近的巴音门肯听过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长达4个小时的训话。据别人讲,他年轻时也是很威风的,骑着走马,后面还跟着背着枪的警卫员,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是多大的官职,能享受到如此待遇。后来两个乡合并,让他到合并后东胜县的扁担梁继续工作,他提出自己家里没有人手,生活困难,辞去了副乡长一职,回家务农。他现在说,当时这一决策非常正确,解放后当时那些乡里的乡长,不是坐监狱,就是枪毙,没有几个能够幸免的。等到我懂事了,文化大革命也很快开始了。当年的那些往事不但不能显摆,完全成了一大罪状,名正言顺地给你戴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踩上千万只脚!
父亲在锡尼补拉相继当过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领导。当年锡尼补拉成立的牧业社是杭锦旗第一个初级社,他任过社长。由于他在农业生产上很懂行,又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所以在农牧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特别是和当地的蒙古族群众,关系相当好,很有人缘,得到人们的拥护和支持。这期间,可能是1951年吧,他曾被召到供销社工作。上了半个多月班后,考虑到我母亲一人在家操持家务,又要照料奶奶,拉扯我们姐弟俩,实在忙不过来,就主动辞职回家。要不他也是拿工资的公职人员,说不定还有很好的发展空间。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可我从来没有听父亲抱怨过什么。
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虽然早已宣布退出国民党,但由于他是旧职人员,即使是内蒙古自治区“九·一九”起义人员,有北京军区颁发的“起义证”,但那时是不认那些的!他自然首当其冲,很快被关进了牛棚。记得那是1966年的冬天,我从北京串联回来后回家过春节,父亲当时虽然还没有被关进牛棚,但已被批斗过多次了。暂时仗着人缘好,还让回家过春节。半夜,我们一家三口正睡得香甜,突然一群红卫兵闯进来了,要在我们家开个现场批斗会。我也被迷迷糊糊地喝叫了进来。批斗完后,还对我进行了教育,要我和家庭划清界线,反戈一击……
正月初二,父亲怕我在家跟着他受牵连,看着他批斗心里难受,就让我出外地继续串联。因为当时全国红卫兵坐火车、汽车的大串联停止了,各地正热火朝天地搞徒步串联,学习当年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组织了很多支徒步串联队伍,谁也可以组织,只要有几个人,学校就给开介绍信,去了任何地方都必须认真接待,提供吃住方便。正月初二我离开家时,早上父亲把我送出门,我看到父亲在一旁偷偷抹眼泪,那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父亲掉眼泪。到了锡尼镇后,我准备和同学们去延安串联,但最终因我们几个同学怕徒步太辛苦、胆子也小怕走失而作罢。而我的二哥韩守俊他们伊盟师范学校组织的红卫兵长征队却徒步走到了武汉,回来给我一说,真让我羡慕和后悔死了!
我走后不久,父亲就被关进了牛棚。白天劳动改造,晚上接受批判。和他一起关在牛棚的有一位蒙古族青年,叫达木林,因不堪忍受无休止的批判、无情的羞辱和繁重的体力惩罚,一天晚上便要上吊自杀。被我父亲发现后,我父亲就劝他,你这么年轻,才踏上人生的道路,哪能就结束自己的一生呢?我已经老了, 我还不想走那条路呢!达木林听从了父亲的劝导,坚持了下来。文革后,达木林就任过杭锦旗党委副书记。他非常感谢当年父亲对他的劝导,经常说,是父亲救了他一命,没有我父亲,就没有他的今天!
我的父亲一生十分节俭,母亲十分贤惠,而且也特别会过日子,精于操持家务,而且做得一手好饭菜。在我印象里,母亲最拿手的是蒸馒头、压粉条、擀豆面、做荞麦凉粉、生豆芽、做米酒、炖肉等,那技术水平是一般妇女达不到的。馒头又白又煊,放的碱恰到好处;压出来的粉条既精又白,每次压粉条的时候,我都要乘热捞出来调上醋、酱油吃上两碗。特别是用荞麦糁子做的荞麦凉粉,那真是绝了。从我母亲去世后,在山南海北我都品尝过各地的凉粉,但我再没有吃过母亲做得那么好的凉粉。
后来尽管陆续遇上了大跃进和60年的大饥荒,家里除了和别人家一样,难免吃粮咽菜,但总是要比别的家庭过得稍好一些。母亲把饿死的羊羔捡回来,剥洗干净,吊在凉房里风干,炖上一点儿也能解馋;把土豆煮熟切成片晾干,作为我上学的零食;把苦菜、野沙盖、沙葱腌在菜瓮里,解决牧区蔬菜缺乏的困难;把棉蓬籽、沙蓬籽打回来后,掺和在玉米面里,以解决主粮不足的问题。我的奶奶那时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父亲对她特别孝顺。所以家里有点顺口的,好吃的,基本都是我和奶奶独自享用。实在紧张的时候,宁可让出作出牺牲,也不会让奶奶受了委屈,当然这时奶奶一定会偷偷从碗里给我分一点儿好吃的。
父亲的手特别巧,像母亲做的衣服,都是由父亲给她结桃疙瘩扣子。桃疙瘩扣子是用布条编成的,编出来后既要圆又要好看,就和现在编的中华结一样。父亲还会织羊毛袜子,后来又学会了织毛裤。老年以后又学会了编菜篮子。他用塑料条编出来的菜篮子,既结实又好看,上面还设计了一些好看的图案,我们姐弟及周围邻居家都用过他编的菜篮子。
父亲杀猪宰羊更是一把好手。那时候家家都养猪,到了东胜后,母亲每年还照样养猪。而每年杀猪,我是帮不上手的。就连压猪也笨手笨脚使不上劲儿。父亲一看我那样子,往往生气地说,什么也不会干!我心想,我不会干,还不是你惯的。记得有一年从牧区拉回来的羊,杀的时候剩下一只怀了羔子的母羊没有杀,结果几年的时间,就繁殖到8只。因为在羊多了在城里饲草无法解决,父母年纪大了也没有精力照料,所以要一次性宰杀掉。那年他已是70来岁的人了,还能一口气杀掉8只羊。当时我舅舅帮他杀羊,我舅舅比他要年轻,他还嫌他手脚脚慢。他宰杀、剥皮,倒肠肚、卸解肉,特别利索,我看了一是羡慕他健壮的身体,二是钦佩他娴熟的宰杀手艺。
父亲年轻时特别喜欢骑走马,还当过大队的民兵骑兵连长。那时候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养过好多匹走马。养走马的成本很高,首先要有好草,必须是谷草,用铡刀铡得又细又碎、干干净净,不能有一点儿泥土;还要有好料,最好是碗豆,最次也要喂黄豆、黑豆料,碾碎了后头天晚上就用温水泡上,有时为了下火,早上还要让我往里撒一泡尿。好马还要有好的笼头、鞍鞯等装备,一点儿也不能含糊,就是所谓的“好马配好鞍,好女配好男”。因此我们家的走马是全大队和书记、大队长能够媲美的最好的走马。但是父亲的走马我却没怎么骑过,因为我不会骑,驾驭不了,父亲的走马大多又高又大,性子烈。只有一匹二岁子小走马让我骑过一回,还是父亲硬把我抱上马背的。我记得是去赶“交流”。从我们家到锡尼镇,虽然只有40里路,但我骑在马上却出了一身又一身冷汗!
我们家居住在牧区几十年,生活习惯也完全同化为蒙古族牧民的习俗。吃糙米、吃奶食品、炖羊肉、手把肉、穿羊皮衣服、皮裤,盖羊皮被子、铺羊皮和狗皮褥子,父亲更是和大多数蒙古族牧民成了朋友,学会了简单的蒙古语。2009年,一位当年的蒙古族牧民还特意从锡林郭勒盟赶来看望他。他叫康满,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他说,我离开锡尼补拉后,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就是特别想见见韩老汉!他是个好人!
父亲现在虽然是90多岁的老人了,但脑子一点儿也不糊涂,思想能赶得上时代的步伐,跟得上形势,他看问题、分析问题精辟入理,处理事情滴水不漏,头头是道,十分公道,得到了族人的一致信任,被韩氏家族推举为家长。后来因年事已高,才逐步推掉这一责任。
他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在所难免,除了耳朵有点背之外,大的疾病基本没有。这和他一辈子不吸烟,少量饮酒、不暴饮暴食和长期参加体力劳动有直接关系。
父亲是1976年从牧区把户口迁移到东胜的。那时我和姐姐都在东胜工作,当时由于交通不方便,对二位老人的饮食起居难以照顾,经过再三劝告父亲才同意告别了那片生活了30年的热土和熟稔的乡亲们,搬到了东胜居住。到东胜后他也不愿意依靠我们,而是以近60的年纪曾经在建筑工地干过活儿,后来在我们的干涉下,自己又找到在东胜县政府烧锅炉、打扫卫生、下夜的活儿,后来又到地毯厂干了几年下夜的工作。80岁前后又在自己家里开了几年棋牌室,他给来玩儿的邻居们熬好茶,出去买香烟、食品,服务得很到位,招徕了很多固定的客户。直到2009年秋天搬到老年公寓之后,才真正开始安享晚年。可以说,这辈子父亲基本没有依靠过我们,直到现在,他已是91岁的老人了,仍然自食其力。只是在身体有了毛病时,才让我们领着看看医生。
2009年他的房子拆迁后,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去老年公寓。他的这一观念和现在大多数老年人完全不一样,比起那些老年人不知要开放和进步多少年!一些老年人认为有儿女在,让老人去老年公寓,是对老人的不孝敬。而我的父亲认为,自己的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要寻找自己的生活乐趣,和老年人在一起,能玩儿在一起,说在一块儿,相对又比较自由。再说现在的老年公寓,条件都比较好,卫生、医疗、服务、饮食等,都比较适合老年人入住。我们做儿女的,都还没有那个思想准备,在传出父亲居住的房子要拆迁前,他早已考察好了适合他入住的老年公寓,等拆迁手续一办完,他一天也不耽搁,就搬到位于旧塔拉壕乡的老年公寓了。
在老年公寓里,他其乐融融,每天和一帮老年伙伴们打麻将,散步,生活得有滋有味。其他老人见了我就说,你父亲脑子真好,打麻将谁也打不过他!太厉害了!每当看到其他老人,特别是那些比父亲年纪小,但走路歪歪斜斜,说话口齿不清的老人们,我们从心底深深感到,我们做儿女的能有这样一位聪明健康的老人,真是上天给我们最大的恩赐!也是我们韩家祖上有德、荫庇后世,父亲一生积德行善、修下的福分啊!
父亲一辈子温顺善良,性格比较急。2009年旧房拆迁时,周围的邻居都想乘机多要点拆迁费,所以千方百计拖延时间,寻找一些理由多要一点儿钱。而我父亲则主动与开发商联系,要提前签字。我们说这些事情你老就别操心了,你去老家散散心。可是他着急得晚上觉也睡不好。我们说,人家开发商还不着急,你着的什么急?可是他不行,一定要签了字,才肯回老家。还说,钱有多少是个够,差不多就行了!我们怕因为多要一点儿钱而让老人家发生什么不愉快,别再急出什么病来,就依他的意思先于左邻右舍和开发商签了字。而补偿的拆迁费,他除了给自己留下少部分养老金外,其余的全分给了我和姐姐,并且还给了我的女儿和大外甥每人1万元。
父亲一生总是为别人想得多,为儿女子孙们想得多,特别是对家庭的责任,对父母的责任,他是丝毫不懈怠的。他对奶奶的孝敬、抚养,有目共睹,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我女儿上大学期间,每年开学临走之前,他还要给女儿一千元钱。
因为他没有固定收入,钱不在多少,表达了他对孙女的一片真情!我女儿结婚时,他又去订做了一块双人床纯毛地毯,作为孙女的陪嫁。地毯的图案也是父亲自己选择的,大红底色上一朵盛开的牡丹,表达爷爷对孙女富贵吉祥和幸福安康的祝福!
父亲一辈不愿意求人,即使在生活上也尽量靠自己的所能,过一种平淡、普通和知足的生活。所以,可以说父亲这一辈子付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付出了艰辛努力,付出了劳动汗水,才收获了一个充实的人生,无怨无悔的人生,幸福快乐的人生!
(韩守忠)
轮值主编:成才